攝影藝術家 蔡定邦|從攝影中開始自我覺察與探索人生
自我探索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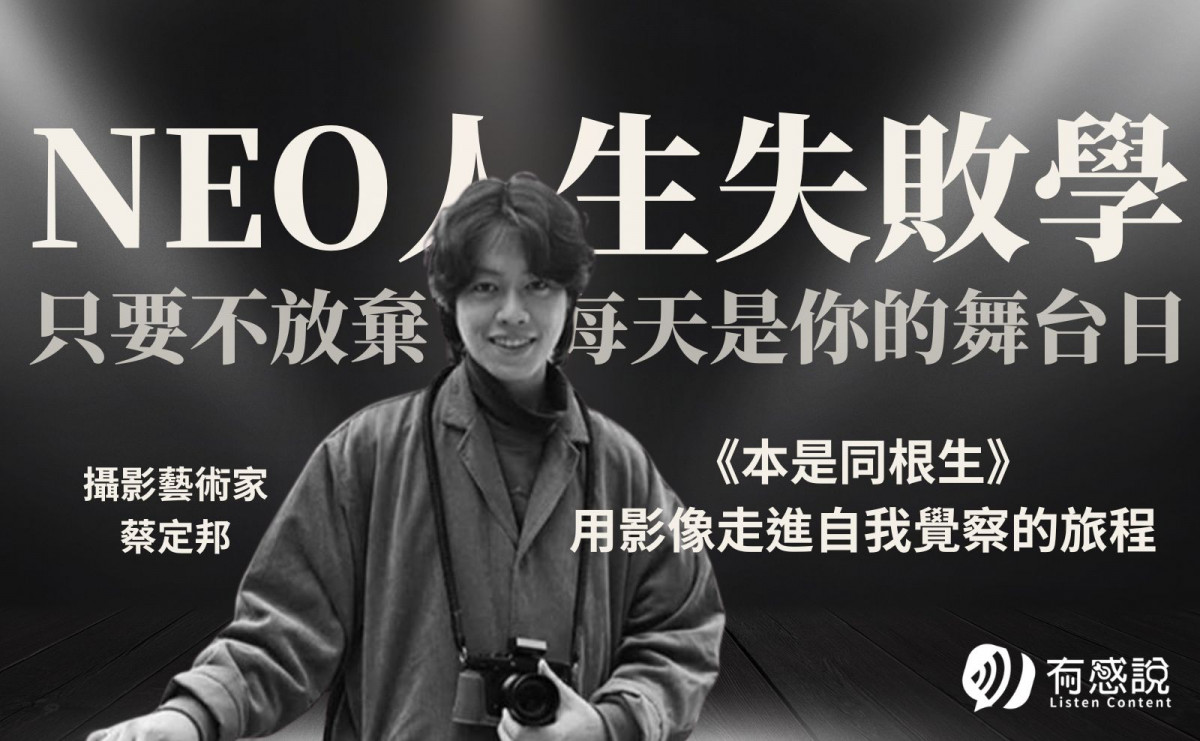
在創作的世界裡,最動人的故事,往往不是成功的榮耀,而是那些從黑暗中摸索出光的瞬間。 這一集《人生失敗學》,我們邀請到一位以生命拍照、用影像思考的年輕攝影藝術家—蔡定邦。他以攝影書《本是同根生》榮獲巴黎光圈攝影書獎(Paris Photo–Aperture Photobook Awards),成為台灣首位得主;並入圍2023 阿爾勒攝影書獎與2024 新加坡攝影節 Dummy book Award。 但在這些光環背後,藏著的不是一段順遂的藝術路,而是一場漫長的自我覺察與情感探索。 一、一通電話,開啟了「拍下自己」的旅程 故事的開端,其實平凡到不能再平凡—那是一通電話。 多年未聯繫的哥哥,因車禍住院,急著要他回家幫忙拿藥。當蔡定邦推開房門的那一刻,看見的是一個幾乎無法落腳的房間,與一袋袋整齊疊放的藥袋:憂鬱症、失眠、失覺失調、安眠藥……那一刻,他感覺自己「踏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」。 那不是對哥哥的指責,而是一種震撼。他突然意識到,原來彼此雖是血脈相連的家人,卻早已活在截然不同的宇宙裡。於是,這個瞬間成為他創作的起點。《本是同根生》就此誕生一部以兄弟為雙主角、以家庭為底色的攝影書。 二、雙開形式,類似又不同的靈魂 《本是同根生》是一冊特殊的雙開書。打開時,你會發現它由兩個方向展開:左邊是「我」,右邊是「哥哥」。他希望觀者能同時翻閱、同時呼吸,讓兩條生命線在節奏中交錯、互相照映。這不是一個「記錄疾病」的作品,也不是對家庭的控訴。他說:「我想把哥哥拍成一個正在努力生活的人。」每一張影像,都在問一個更深的問題—「當我們看見他人的脆弱時,是否也在照見自己?」 這樣的設計,也象徵他與哥哥之間的連結:一邊是光,一邊是影;一邊是行走,一邊是靜止。兩個人既對照又共鳴,就像我們每個人內在的雙重性——堅強與脆弱、明亮與黑暗。 三、家庭檔案裡的情感線索 作品中穿插大量家庭舊照片。那不是懷舊的佐料,而是一種線索。在嘉義老家的照片堆中,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從小,兄弟倆的差異就早已被鏡頭捕捉下來。他笑著說:「我每張照片都在笑,我哥每張都不笑,連畢業照都皺著眉。」 這些照片成為他重新理解家庭的起點。他開始思考: 家,是不是我們最早學會掩飾的地方?而攝影,是否能幫我們重新誠實一次?在挑選影像時,他不只是技術地構圖,而是情感地對照。他刻意讓歡笑與陰鬱並置、明亮與暗角並存,就像人生本身,不是被分割的黑白,而是彼此滲透的灰階。 拍攝哥哥的過程,也讓他學會了「界線」。每一次按下快門前,他都先問:「這張照片你可以嗎?」他說:「我不想替他定義,我想讓他參與。」 哥哥看著照片時,會以導演的視角討論—「這裡的張力不夠,再暴力一點。」 那一刻,蔡定邦發現創作不只是紀錄,更是一種共同創造的療癒。這樣的理解,也延伸到他的人際世界。他曾是被排擠、被誤解的孩子—自學成長、從十二歲就被同學孤立、被說「講話很賤」、十五歲開始打工、十九歲拍片失敗。他笑說:「我那部短片,唯一被稱讚的是攝影很好,偏偏攝影師不是我。」那份被忽視的挫折,成了他重新學習「如何與人相處」的契機。 他開始大量閱讀管理學與溝通書籍、練習「三明治溝通法」、研究老子與中庸之道。這些理論後來變成他的生活工具,幫助他在咖啡店的工作裡學會帶人、理解人、對話人。他說:「以前我只想讓人懂我;現在,我想先懂別人。」 四、自學者的覺察:我拍的不是哥哥,是自己 從電影夢的失敗,到攝影的被看見,蔡定邦走過的,不只是職涯的轉折,更是心的轉向。他坦言:「我拍哥哥的同時,也在拍自己。那個孤獨、那個想被理解的自己。」 這份自我覺察,讓他不再急著去「修復」什麼,而是學會與現實共存—與病症共存、與不完美共存、與過去共存。 「以前我以為創作是逃避,現在才知道創作是回家。」他說這句話時,語氣溫柔卻堅定。 五、失敗學裡的光 對蔡定邦而言,「失敗」從來不是終點。那是一種提醒—提醒我們誠實面對自己。 在節目最後,他分享了三個陪自己走出混亂的信念: 1.停止內耗。不要急著替別人解讀語氣與表情,很多時候,那些「誤會」只是我們腦中的放大。 2.換個角度理解。先試著站在對方的位置看世界,尤其是當你最不想理解的那個人。 3.說出來,就是一種自由。無論是一句話、一張照片、一個擁抱——只要你願意表達,痛就開始有了出口。 六、一句話,給仍在黑暗中的你 他對聽眾說:「如果你也在經歷家庭的混亂、關係的疲乏、或與自己的失聯,試著打那通電話、寫下那句話,或丟掉一個耗損你的習慣。因為當你願意表達,代表你開始理解,也開始變得自由。」 這一集《人生失敗學》沒有華麗的結論,只有一個溫柔的邀請—讓開口,成為你與自己和世界重新連結的開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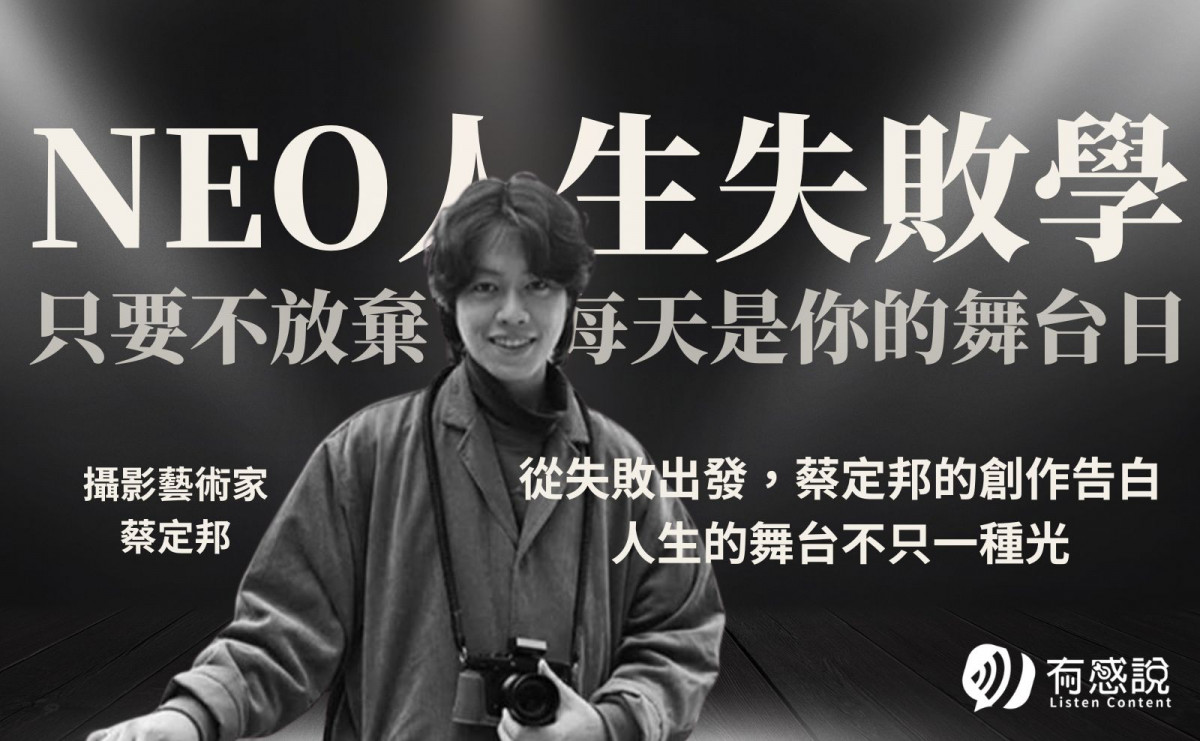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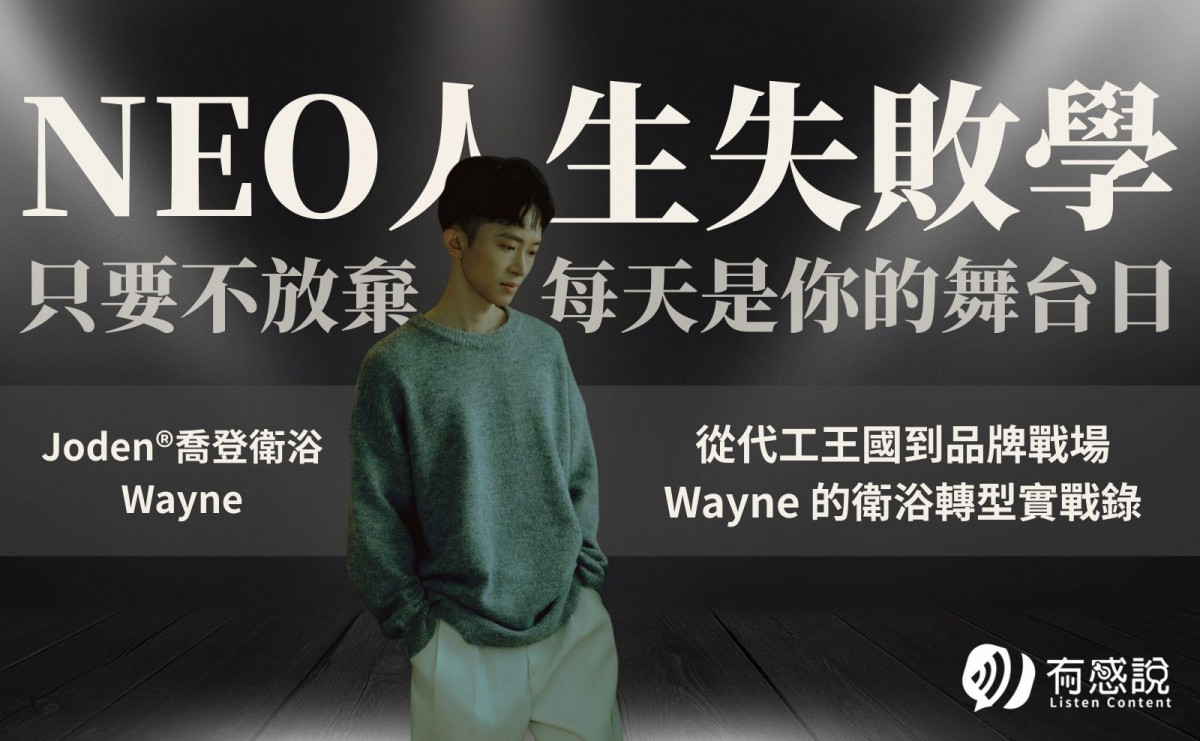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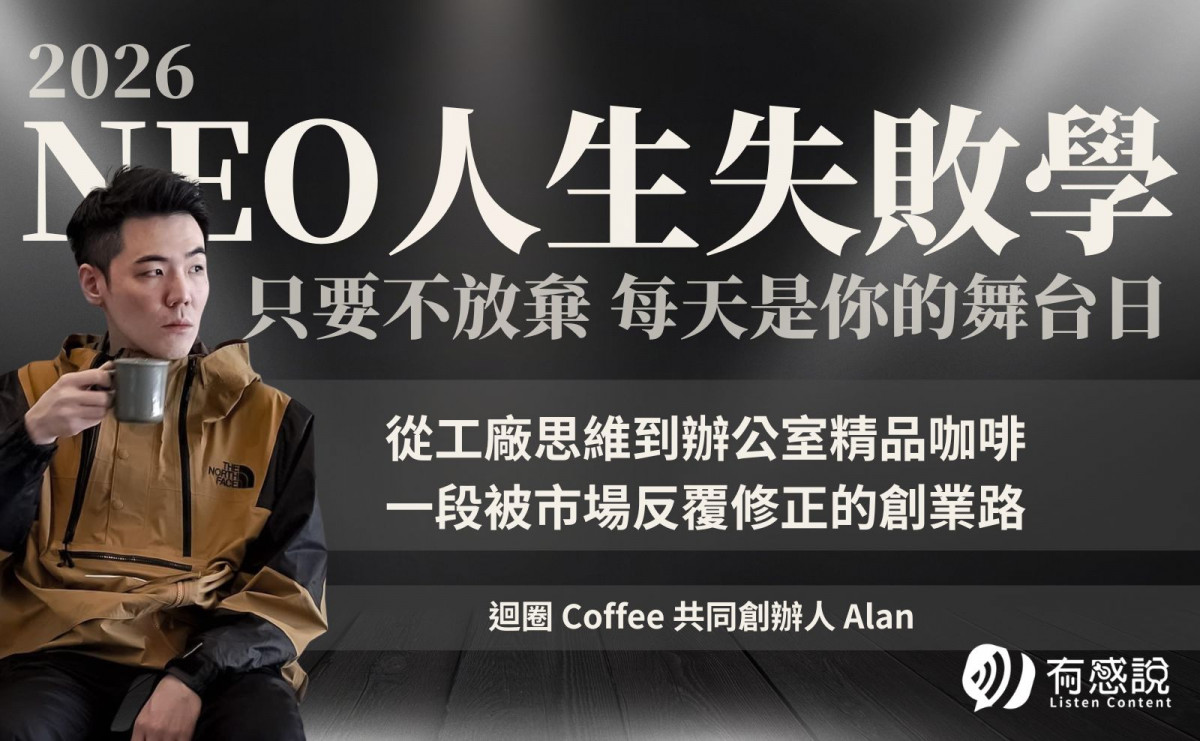

 Google快速註冊/登入
Google快速註冊/登入